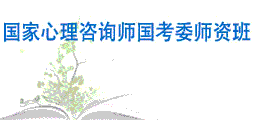在弗洛伊德的模型中缺乏的概念表现为阳具的缺失。想与母亲同床的男孩是想以他的阳具填充她而弥补其缺失。弗洛伊德认为对于男孩而言打断这种俄底浦斯欲求的是父亲,他以阉割相威胁。父亲威胁男孩如果他试图用阳具弥补母亲的阳具的缺失就将经历缺失,即阳具的缺席。以拉康的话说阉割威胁是一个对于缺口整体概念作为一个结构概念的隐喻。对拉康而言不是现实的父亲以阉割相威胁。相反,由于缺乏的、也就是缺口的概念为语言的概念所必须,由于缺口的概念是语言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所以父亲就成了语言学结构的一个功能。
阳具,石祖与父亲。
父亲不是一个人,而是象征界秩序的一个结构形成的原则。对于拉康而言,弗洛伊德所说的怒气冲冲的父亲变成了父亲的名义,或者父亲的法律,有时干脆就是法律。只有服从了语言自身的规则——父亲的法律——才能进入象征界秩序。为了成为言说的主体你必须屈服、服从于语言的法律和规则。拉康将语言结构的概念和语言规则看成是特别的男性化的。他称语言规则为父亲的法律,其目的是将象征界的、语言规则的入口与弗洛伊德的俄底浦斯情结、阉割情结联系起来。父亲的法律,或者父亲的名义,只是叫法不同,其实就是大它,是系统的中心,是那个控制着整个结构的东西——控制着结构的样式、控制着系统中所有元素怎样运动、怎样形成关系。
此一中心也称石祖,甚至奠基了象征界秩序的父权性质。石祖作为中心约束了元素的游戏,赋予整个结构以稳定性。石祖锚定了能指链,在无意识中能指链漂浮不定、不断地滑动和漂移。石祖阻止了游戏,能指因此而拥有些许的稳定意义。正是因为石祖是象征界秩序的、亦即语言的中心,所以“我”这一个词就能够指称自我的概念(并且附带地所有其它的词也因此而拥有稳定的意义)。
石祖不等同于阳具。阳具属于个体,而石祖则是属于语言自身的结构。没人拥有石祖,就如没人能够控制语言或者语言规则。相反石祖就是中心。它控制了整个结构,它是每个人都想成为的(或者想拥有的),但是没人能够达到它(系统中的任何元素都不能取代中心的位置)。这就是拉康所谓的欲求:永不被满足的、永不能够被满足的、成为中心的、控制系统的欲求。
拉康说男孩们认为自己有过一个尝试去成为石祖、去占据中心的位置,乃是因为拥有阳具。女孩们要做这样的尝试就困难多了,乃是因为她们(如弗洛伊德所言)生来就有、就是缺乏,即缺乏一个阳具,而石祖则是一个场所——在那里什么都不缺。然而拉康说每个在语言中的主体生来就有、就是缺乏,即缺口。我们拥有语言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丧失、缺乏与母亲身体的合一。事实上正是这种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语言中的主体的急迫性促成了上述的缺席、丧失、缺乏。
两性区分在拉康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不是弗洛伊德的意义。他曾在《无意识中字母中介》一文中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两扇相同的门(所指),门上的字不一样,一个写“女厕所”,一个“男厕所”。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小男孩(哥哥)和一个小女孩(妹妹)坐在火车的包厢里,面面相对,靠着窗口。火车启动了,站台上的建筑一一闪过。
哥哥:“瞧,我们到了女厕所!”
妹妹:“白痴!你难道没看见我们正路过男厕所。”
这个故事表明男孩与女孩进入象征界秩序、进入语言结构的方式如何不同。拉康认为每一个孩子只能看见异性的能指;作为看见“它者”的结果,每一个孩子都在构造它自己的世界观、构造它自己对于男女厕所的命名、以及对于在此命名过程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拉康说,“对于这些孩子而言,男厕所和女厕所成了两个世界,孩子的灵魂扑打着翅膀努力接近对方的世界。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确定的性别,在象征界中具有一个具体的位置;每一性别从这个位置出发都只能看见(也就是指称)异性的它者样态。可以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拉康所说的两扇门:它们区分性别,每一个孩子必须通过各自的门才能进入象征界。
七、总结
拉康理论的起点是现实界的概念,现实界是与母亲身体的合一,是一种自然状态,必须被打破才能建构文化。一旦离开现实界人就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却总是想回去。这就是不可逆丧失或者缺乏的概念。接下来是镜象阶段,它构成了想象界。在此要明白它者的概念,明白大它存在作为一个概念或者结构形成原则,并由此构造“自我”的概念。这个“自我”(如同在镜子中所看见的)事实上是一个它者,你只不过是将之错认为你了,并称之为“自身”(或者通俗地说,你照镜子,你说“瞧,那是我”,可并不是你,它只是一个图象)。
这个自我感及其与它者、与大它的关系使得你开始在象征界秩序中、在语言中找到一个位置。这一位置允许你说“我”,亦即允许你成为一个言说的主体。 “我”(以及所有别的言词)具有一个稳定的意义,因为所有的言词被大它/石祖/父亲的名义/法律——后者是同一个东西,是象征界的中心、语言的中心——所固定、所锚定。在落入象征界的某个位置的过程中你得经过一个有性别标志的门廊,女孩子的位置不同于男孩子的位置。男孩子比女孩子更靠近石祖,但是没有人是或者有石祖——它是中心。
你在象征界的位置如同所有别的能指元素(能指)的位置一样是被石祖所固定的,与无意识不同的是,在象征界中的能指链并不无休止地循环和滑动,因为石祖限制了游戏。滑稽的是——即使尚未糟糕透顶——石祖与现实界特别相似。二者都是圆满的、完好的、具足的、统一的,毫无缺乏,毫无缺口。二者都是活命于语言中的人类主体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二者也不同:现实界是母性的,我们所由诞生的土地,我们为了拥有文化而从中分离出来的自然;石祖是父亲的概念,是文化的父性秩序,是文化的终极概念,是左右世上万事万物的制高点。
作者比较清楚地陈述了拉康的部分观点,但是陈述中的某些内容似欠妥当。比如缺口,拉康认为缺口是先天的,是出生之际就存在的,正是由于缺口的存在,所以现实界中才有需求,想象界中才有分离,缺口才是真正的锚定。而这又引出所指存在的问题:作者在文章的前部分说拉康理论中完全不存在所指,在后部分说存在所指,而且对于此陈述上的不一致未加讨论或者说明。这当然与拉康理论本身也不无关系,其言说风格之飘逸、涉及的问题之复杂、特别是在母亲地位问题上的不明晰,都增加了后学理解他的难度。
[1] 作者系英语副教授,工作单位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译文作了分段并加了小标题。
[2] 本文用了ego和self两个单词,本文均译为自我,区别是前者写作“自我(ego)”,而后者不标英文。
[3] 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问题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在科学的框架下自由意志也许只是一个虚象,也许一个十分粗糙的说法是在决定论的前提下随机涨落引入了一种对于外部影响的可塑性,从而表现出自由意志。但是这个说法中决定与随机两个概念在近代物理学中本身就是一对难以兼容的范畴。
[4] 事实上拉康继承了更多的思想传统,例如笛卡儿和黑格尔。
[5]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上有分歧,一是认为它我所在之处,自我一定也在场,即这是一种人格结构的特征;二是认为它我所在之处,理想的情况是自我也在场,即是神经症的治疗目标。后一种理解令人想起禅宗大师百丈怀海所说的 “宁为心师,不师于心”。(《古尊宿语录》百丈怀海条下)
[6] 它我:即Id,中文有译为本我,实际上Id是拉丁文,相当于英语的it,即“它”,故霍大同先生准确地指出此术语应译为它我。
[7] 同一性:即identity,指一个人的根本而连续的自我,关于一个人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内部的主观的概念。
[8] “我”自己:“I”self。
[9] 准确地说拉康不是不讲所指,只是强调能指,不怎么注意所指。
[10] 价值:value,是索绪尔引入的一个概念,说明一个结构中的元素通过结构中的元素相互之间的否定性关系而获得了指示性价值。详见氏著《普通语言学教程》。
[11] 结构主义的基础在于两个对立性元素的相互关系构成基本结构,而德里达指出结构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是线性的,结构是由一个作为中心的基本结构将其它的成份加以组织起来的,并且基本结构中的对立性元素的任一个是其对方的一部分,这破坏了A与非A的基本对立关系,从而“结构坍塌”,人们可以借助这一方法揭示任何一个现存结构存在与自身逻辑相矛盾的事实,这既不是重建结构,也不是消除结构,而是“解构”结构。用通俗的话说,意义不存在,但是我们可以“仿佛意义存在似”地活着。
[12] 需求、请求和欲求:need, demand and desire。
[13] 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the Real, the Imaginary and the Symbolic。
[14] 缺失是对需求的存在性表达,需求是对缺失的动力性表达。从需求到请求的标志是哭叫——语言引入。
[15] 小它:英语为other,法语为autre。本文中常常用到的“它者”实际上是“小它”,之所以未直接译为小它是为了强调“它者”性。读者请注意这一点。所谓的小它,是欲求的对象,例如微笑、注视、乳房、奶嘴。
[16] otherness:本文译为它者存在,个别地方译为它者样态。
[17] “我”同一性:“I”dentity,这是本文作者玩的一个游戏。
[18] “自我”就是“它者”:这是一个德里达式的陈述。
[19] 大它:英语为Other,法语为Autre。